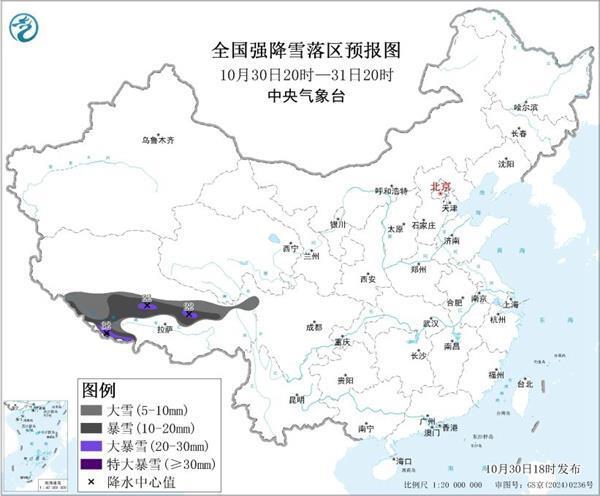1、原材料较单一(土 木 陶 骨 玉) 形制较粗狂,多采用夸张手法,原始崇拜因素较多。

2、表现事物种类较少,多为生殖崇拜,渔猎耕作和祭祀为主。
3、艺术载体单一,多描绘和雕刻在日常用具上。
4、也有一定量的饰物出现(骨链等) 但专门艺术品还未大量出现。
旧石器时代的美术主要体现在石器工具上新石器时代陶器在实用性的前提下,发展了美的造型和装饰,所以新石器时代的美术绝大部分都与陶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也在陶器的造型和装饰上得到表现。
继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之后的磨光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以磨和钻孔技术和极整齐对称形式成为石器工具发展的高级阶段。
先民已有多种多样的审美创作活动,我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装饰品,是约三万年前的一件石墨装饰品,中央有穿孔,可系绳佩挂。钻孔是人找到深度和厚度的劳动,钻孔突破平面,发展了第三空间,是雕塑造型的基本因素。山顶洞人已采用赤铁矿粉末与红色泥岩作染色材料。
中国原始艺术展览有哪些
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类型文化,是继承老官台文化发展起来的。半坡文化的彩陶上有较多的动物图像,描绘了奔趋的鹿、爬行的鼋(亦称蛙或龟)和伫立的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花纹是鱼类纹,数量最多,并贯串于半坡类型文化的始终。半坡早期彩陶上鱼类纹的形象较写实,常见的是单独的鱼纹,多为平展的侧面形象,以直线造型,比例虽较准确,然略显平板。

陕西省临潼县姜寨一期遗址第159号墓出土的彩陶大盆内,画着大致作一圈排列的5条鱼,是用两种不同画法画成的:①为黑色影像,突出鱼的外廓形象;②用线勾出鱼的各部分,并结合运用黑、白映衬的手法。中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富于变化,因其造型系以直线与弧线相结合,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运用,故使鱼纹显得活泼灵动。其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蹦跃等姿态。姜寨二期遗址出土的尖底彩陶罐上的游鱼图像,夸张地表现出游鱼回首返泳的瞬间动态。甘肃省秦安县王家阴洼半坡类型墓地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环绕腹部画着4条不同姿态的游鱼,或舒展平泳,或俯冲疾下,或相对背向地屈身蹦腾,构图活泼,堪称原始绘画的佳作。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鱼纹头部的变化最大,突出表现了张大的嘴和露出的牙,鱼纹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而且鱼纹用弧条形统一造型,趋于几何形化,富有装饰性。
人面纹也是半坡类型的文化彩陶上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纹样。甘肃省正宁县宫家川和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各出土了一种在瓶腹上满绘着人面图像的葫芦形瓶。人面獠牙突露,双目眦睁,威武猛厉,表现出超人的勇力。
半坡早期的彩陶上,还有两种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奇特形象:①鱼寓于人面的复合形象。人面的嘴的两旁对称地各衔一鱼,人嘴外廓与鱼头构成共鱼形;②人面寓于鱼的复合形象,在鱼纹头部圆框中填入适合形的人面图像。这种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人和鱼互相寄寓,又互相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类图纹可能是半坡部族的图腾,具有氏族保护神的性质。在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半坡类型文化的彩陶纹饰中,还出现了十分奇特的鱼、鸟结合的图像和鱼、鸟、人面的复合形象。武功县游凤出土的细颈彩陶壶的腹部上,绘着鱼衔鸟的图像,经过夸张变大的鱼头中,含着一个圆睁着眼的鸟头,以此意味着鸟寓于鱼。而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一件彩陶壶上,则用均匀的粗线绘一衔鱼的短尾小鸟,鱼的形象较奇特,身有大片鳞甲,鱼头两侧有突出的鳍状物尾小分叉,此鱼的形象与中原龙山文化彩绘陶器上的蟠龙纹大致相似。姜寨二期遗址第467号灰坑出土的葫芦形彩陶瓶的腹部上,画着鱼和鸟、人面纹巧妙地组合成的图像。图像分上、下两组,上组的上方有3个三角形的发髻,下方在呲牙的方形鱼头中含着人面和鸟头;下组图像是方形的鱼头中含有鸟头。在瓶腹两侧还绘着鱼纹、鱼身纹的复合纹样。可以看出在这件彩陶瓶的组合复杂的图像中,鱼是主题形象,而鸟头和人面是寄寓于鱼的。 距今约6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3省交界。庙底沟早期彩陶以自然形的鸟纹为主,鸟纹为影像式。在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出土的彩陶盆、钵腹部绘着侧面鸟纹,长尾翘举,双翅展起,是鹊类的形象。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庙底沟晚期墓葬中,有一件彩陶缸的腹部也绘着鸟含鱼的图像。画面高37厘米,宽44厘米,占满了筒形腹部的一半,是彩陶上仅见的大幅画面。鸟有长喙,高脚,短尾,通体白羽,是鹳鸟的形象。鸟嘴叼着一条大鱼,鸟眼圆睁有神。在鹳鸟的前方,画着一把立置的长斧,斧柄上绘着X状标号,可能是象征着权威的器物。这幅画的表现技法较为丰富,白鹳用没骨法画成,鹳眼、鱼和长斧的轮廓用黑线画出。笔法多变,苍劲有力。鹳鸟形象比例准确,神态生动。这幅鹳鸟含鱼图是原始社会绘画的杰作。
鹳鱼石斧罐纹样(河南临汝县出土)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河南省博物馆藏)
半坡类型文化彩陶上的鱼类水族图像和庙底沟类型文化彩陶上的鸟类图像,大概都是图腾艺术的表现。在与这两种类型文化邻近和交叉地区,彩陶上还出现了鱼和鸟相结合的图像,是半坡部族和庙底沟部族互相影响、融合而在绘画中的反映。 距今5000年左右,分布在甘肃省东部。石岭下类型的彩陶以鲵鱼纹具有特色。早期鲵鱼纹多为单独纹样,形象写实,呈弯曲状,像在摆动地爬行。甘谷县王家坪出土的彩陶瓶上的鲵鱼图像,形态逼真,但头部似人脸,嘴部有须,只有两足,是人格化的鲵鱼形象。这幅鲵鱼图像的细部画得较具体,脸部、爪指和身上的网状花纹都用劲挺的细线勾勒而成,绘画技巧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提高。武山县傅家门出土的彩陶瓶上的鲵鱼纹,图像已趋于几何形,弯曲的身子概括成月牙状。石岭下晚期彩陶上的鲵鱼纹已几何形化,成为标志性的纹样。
与石岭下类型年代大致相当的大地湾四期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罐上绘着罕见的双兽相斗图,用两组情节连续的画面来表现双兽相斗。一组绘两只猛兽怒目对峙,尾巴耸举,正欲奋起相斗;另一组绘两只猛兽已跃起,作格斗相扑状。这以情节连续的画面构成的双兽相斗图是中国连环画的滥觞。而大地湾仰韶晚期居址地画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立的绘画作品。
1982年11月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清理的第413号房基的居住面上,发现了绘着人物和动物的画面。从该房基出土的器物形制和同层位的放射性炭素断代,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该房基为长方形,房基地面和残存墙面都为抹光的白灰面,房基中部偏前为一圆形火塘,在火塘和后墙之间的地面上,有用黑色绘成的两组图画,上组画影像式的人物,能辨认出为横列的姿态相同的两个人,都是双脚交叉站立,右臂下垂而微弯,手中持条状物。头部已漫漶不清,似有长发向前甩起。右面人物的右边还有黑色残迹,也可能在右方还画有一人。下组画面有一黑线方框,方框内用粗线画两个横列的兽类动物,图像模糊,但能约略辨出动物有竖耳(或角)和四肢,尾上翘,可能为虎、犬之类的动物。大地湾房基地画,现存画面长120厘米、宽120厘米。人物画像高14厘米。 距今约5000~4500年之间,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和青海省东北部。马家窑类型的彩陶花纹中,有少量的具有绘画性的图像。有的彩陶盆内的中央画着团鱼纹(亦称蛙纹),鲜明地表现了团鱼囊状尾的特征。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内的人面鱼身纹,是一种图腾纹样,也呈现了由具象的自然形纹样发展为抽象的几何形纹样的过程。
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清理的一座马家窑类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盆的内壁上绘四圈平行带纹,平行带纹至口沿间,绘3组相同的集体舞蹈图像,每组5人,舞蹈者为正面并列的整齐形象,脑后发辫摆动,腰前飘带飞扬,手拉手地踏歌而舞。每组两边舞者的外侧手臂都画成两道,表示空着的臂膀在不断频繁地摆动,是当时画工表现人物连续动作的特殊手法。舞蹈图不仅巧妙地反映出原始人的舞乐活动,也是直接而完整地表现人物活动的最早的绘画作品之一。 距今4000年左右,彩陶花纹以几何形纹为主,但有一种特殊的神化了的人形图像。半山早、中期彩陶上的人形图像较真实具体,两腿分开地叉立,手臂扬起,有的人形图像的周围有谷、糜类的种子,表示神人正在撒种。半山晚期和相沿发展的马厂早期彩陶上的人形纹,逐渐分解,或无头,或无下肢。马厂晚期彩陶上的人形图像已抽象化,肢节和爪指增多,多以人形的某一部分来示意地表现,人形纹愈来愈被神化。
青海省民和县加仁庄出土的偏口壶的腹部上,画着一正一倒的两个人形纹,在人形纹的四周漾起多圈波纹,正列的人形纹的面部似人,而倒列的人形纹的面部却似水族动物,是人格化的水族动物形象。可以看出半山和马厂类型彩陶上的人形纹,不是现实生活的人,而是赋有神力的超人。
除黄河中、上游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彩陶上写实的象生性花纹很少。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石棚山类型,距今4000多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出土的彩陶罐上,曾发现似山羊又似鸟的动物图像。
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彩陶很快衰落,含有礼器性质的彩绘陶出现。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墓地的大墓中出土了一些彩绘陶,彩绘纹样以蟠龙纹为特色,蟠龙纹以朱红色绘于陶盘内的中央。早期蟠龙图像,身子较短,更接近鱼类形象。晚期蟠龙图像,身子变长,是商周青铜器中蟠龙纹的前身。
分布于南北各地的岩画,相当数量产生于原始社会,是原始绘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原始艺术展览在哪里
中国原始艺术是怎么产生的: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决定于观念的产生和演进,艺术的起源表现了原始人开始对人类自由本质的自觉和肯定,对自由的肯定意识蕴含着推动自由发展的愿望,意识和愿望的获得是令我们的动物祖先变成人类的基本因素,通过对人类的起源、艺术的起源和宗教意识的起源的分析、探寻人们对人类本质的自觉的思想源头。在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诸种形式尚未分化和独立,原始意识形态作为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浸透着浓厚的宗教精神,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像意识形态的诸形式一样,艺术的胚胎包含在原始宗教中。在原始社会,艺术存在于宗教中,但并不意味着艺术为宗教所产生。这是因为艺术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原始宗教并不等于全部社会生活。原始艺术不但服务于原始宗教,也服务于原始的政治、伦理、教育等等。原始宗教本身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宗教对艺术的影响,归根结底也反映了经济基础的间接的、但是决定性的作用。原始的艺术与宗教同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同属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在艺术起源中产生作用的各种非根本的因素中,宗教的作用居于突出的地位。从“原始艺术”的内容看,主要反映了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但有一个题材逐渐扩大的现象。在最早的原始洞穴壁画中我们发现的基本是动物的形象,很少有人和植物的形象,到了岩画时代,我们才发现人类的形象第一次大量地出现。这说明早期的原始艺术只关注动物,但随着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日益强大,对动物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小,人们有了其它的生存之道,因此对动物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少。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都用想像的、非逻辑的方式来表现。原始人认为神灵主宰一切,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往往以宗教性的活动或仪式作为开端或结束,宗教色彩渗透着他们的活动过程和思想过程。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巫术等初级形式的宗教活动,是人类原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艺术反映了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原始艺术还不是为着纯粹审美的目的,而是为着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进行活动。这种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常常体现在图腾崇拜或巫术活动中。在这些场合,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在独立的观赏艺术产生之前,原始艺术的各种形式,如歌、舞、剧、绘画、雕塑、诗歌、神话等等,都曾作为手段和形式服务于原始宗教活动的目的,而这些艺术形式也往往是在宗教活动中发展成熟的。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的浑然一休,不但在于二者都倚重幻想、象征和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而且由于二者都有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时至今日,学界对“原始艺术”的研究还在继续深入,相信随着考古学和人类学更多发现,还有更多的神秘将被揭开。